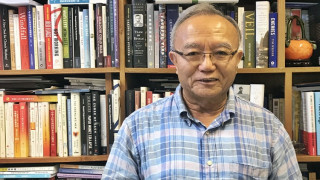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因為反對派拉布,選了半年也選不出主席。另外有大量的政府撥款申請在立法會嚴重拖延。這些事大家初見時都甚覺驚訝,但久而久之,大家習以為常,甚至愈來愈多人覺得反對派拖得有道理,卻不知道自己為拉布付出重大代價,人家拉布,自己找數。
香港陷入一個集體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(Stockholm syndrome)。這名詞源於一九七三年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單銀行劫案,匪徒Jan-Erik Olsson衝入當地最大銀行打劫,事敗劫持四名銀行職員與警方對峙。經長達六日圍困,最後劫匪釋放人質。這班銀行職員長時間聽了匪徒Olsson的故事,對他產生同情,認同其做法。事後警方將匪徒告上法庭,但四名人質不但不願上庭指證,還替他籌款抗辯。後來瑞典警方找來犯罪學者Nils Bejerot研究,發現人質長時期只聽劫匪單方面道理,結果被洗腦,出現這種同情加害者的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。
我很早已經發現,香港政治上出現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,大家聽加害者單方面講故事,久而久之,認同了對方的觀點。
這個病症出現之初,源於一種怕事心態,主要在高官和建制派議員的社群中擴散。遠在十多年前,反對派在立法會開始玩激進,那時激進派仍勢孤力弱,但行為偏激。高官和建制派高層認為,政策法案和財政撥款都夠人數舉手通過,所以採取「你有你講,我有我過」策略,明明自己有道理的也不去論述,因怕被對方搞,所以不出聲為妙。而對方本來沒有甚麼道理,卻拼命論述。公眾不明就裏,偏激意見聽得多,就覺得激進派也有道理了。
尤有甚者,有建制派大佬,善於討好激進派。多年前任由長毛在立法會「表演」,待長毛曝光夠了,循例叫保安請長毛離開議事堂,長毛也欣然合作,表演完就收工走人。激進派有充份曝光機會,愈養愈大,不斷細胞分裂,快速繁殖。背後是建制派大佬為保自己的光環,不斷向激進派放水,終至覆水難收。
激進派由量變到質變,全面佔據政治意識形態高地,恣意扭曲民主理念,毒化香港的「一制」,主要在兩個關鍵地方下工夫。第一、不按遊戲規則辦事。民主本是一個按規則運行(rule-based)的制度,只要按規則進行,即使得出和自己意願相反的結果,也會接受,因民主主義者堅信,按規則辦事才可達到制約獨裁的目標。然而,激進派由議會內玩激進花招,到拉布拖垮議會功能,再到街頭暴力攬炒,最後演化成用天拿水淋人放火的無底線行為。這是有意識一步步升級,最後在宏大理想包裝下,演化成全無底線的衝擊。
這是玩少數人政治的極致表現:我是少數,但我理想最高,我大晒。在反對派夠膽日日講,而高官建制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去講時,少數派歪理變成真理。人質天天被人洗腦,愈來愈多人倒過來同情劫匪。加害者就由少數派慢慢變成多數派。
第二、否定包容。民主制度本質是透過選舉去產生領袖。在這過程中要包容的理念。大多數人支持的領袖勝出,也要包容落選者民情。所以很多外國極其對立的選舉後,勝出者第一篇勝選宣言,往往提出對立的雙方和解,共同管治好一個地方。然而,香港早於二〇一〇年已有人有意識地散播民主不應包容概念,這是本地大肆搞破壞的勇武思想的根源。包容的反面就是仇恨,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中,經常出現「死全家」標語。而一些在區議會選舉勝選的議員,會在辦事處門外貼上「藍絲與狗不得內進」的告示。
當反對派在未能以大多數議席去控制立法會的時候,就用拉布等破壞遊戲規則方式,去癱瘓政府。但當自己成為大多數上台之後,就倒過來用體制暴力壓迫少數對手。這不是民主社會,而是「多數人的暴政」。
香港的一制已被騎劫,病情甚深。(盧永雄)
全文刊於《頭條日報》「巴士的點評」專欄
【專欄】香港染上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
04月1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