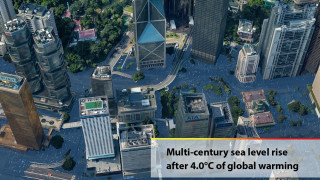去年本港露宿者數量達一千五百八十一人,創十年來新高,其中以油尖旺和深水埗為重災區,西貢區更首度錄得露宿者。有前綫社工分析露宿者增加的原因,除了家庭不和外,近月有一批曾於爆疫後回內地生活的港人,因積蓄用盡被逼回流香港,加入露宿行列;而近年市區重建步伐急速,隨着唐樓清拆令一出,平價板間房也難尋,加上疫情持續兩年,近月失業率雖回落但市道仍未恢復,部分失業人士淪為無家者,希望當局關注。記者 關英傑 仇凱瑭
統計署近日出版的報告顯示,去年全港共有一千五百八十一名露宿者,當中男性佔一千四百零二人,女性則有一百七十九人,較一二年錄得的總數五百五十五人,激增近三倍。根據資料,近十年以來露宿者數字只增不減,以油尖旺和深水埗,合共逾千人,佔總數約三分之二。此外,新界區的露宿者也有快速增長,屯門區增加約七倍最為嚴峻。至於西貢區,更取得「零的突破」,有三人登記。
多年來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衞東估計,現實中有約三分一露宿者,不願向政府部門登記,認為當局掌握的數字低於實際數量。他相信,露宿者增多,或與近年加速市區重建有關,他稱觀塘、油麻地、土瓜灣及深水埗等舊區有不少唐樓,提供數以百計廉價的板間房及牀位,成為不少基層市民的居所,但近年上述舊區相繼有重建項目落成,原有牀位戶當無法在同區找到同類平價住宿,部分人或選擇露宿街頭。
西貢區首錄露宿者
首度被發現有露宿者的西貢區,涵蓋中產社區如將軍澳,同時也包括鄉郊地帶。有前綫社工指,近年確實有數名低調的露宿者,集中在西貢市中心的隱蔽暗角處。有地區人士亦透露,早前他向該批露宿者派發食物及物資,眾人不願多談個人經歷,但透露有打工,其中一人原居於新界,但因在西貢的油站工作,為節省車費,在區內休息,翌日直接上班,待假日才回家。
記者日前晚上到西貢視察,發現市中心有數位露宿者,有人自備輕便的摺疊牀,亦有人以海綿包鋪在設有扶手的公眾長椅上,以便舒適入睡。八旬長者興叔在該處露宿多年,稱因所住村屋被子女霸佔,加上半年前妻子離世,別無依靠下流浪街頭。他透露,近年曾有其他區的露宿者到西貢「試住」,如早前有兩名來自深水埗的露宿者到訪。
近期颱風季,興叔自言見慣大風大浪,稱曾在下雨天與牛共睡,又指若遇暴雨,會到室內躲避,笑言:「十號風球也不怕!」他坦言,曾被社工帶到護老院參觀,但認為院舍無私隱可言,活動範圍狹窄,「外面自在得多,又可以沖涼和涼冷氣」,但他仍然期望,政府能為露宿者安排獨立的公屋單位。
嫌院舍無私隱 活動範圍狹窄
另一露宿者阿海曾任小巴司機,可惜因家庭問題,與妻子不和,亦與子女斷絕聯繫,無奈因缺乏離婚證明等相關文件,無法申請公屋,於一年多前開始到街上居住。阿海患有肝病,也有前列腺等疾病,慨歎身體虛弱,難以找到工作。他躺着回應記者,指淪落街頭,多少有點唏噓,「有屋企誰會想瞓街?希望政府能看到問題,盡快解決房屋問題。」
此外,近年更多了中港兩邊走的市民流浪街頭。吳衞東提到,二○年爆疫初期實施封關,不少奔走中港兩地的港人,返內地與家人生活,但在積蓄用盡後相繼回港。他指,該批回流港人過去從事飲食、運輸及物流工作,但疫下求職碰壁,部分人淪為露宿者,至近期才獲安排居所。

中港兩邊走 疫下宿街頭
「當時山窮水盡,全身只得一百一十元,很淒涼!」四十七歲的女露宿者Balance,前年回內地做小生意,她指內地物價和租金便宜,在深圳可用一千元月租,租住三百呎套房。生意失敗後,她今年五月曾到澳門求職不果,及至六月中當地爆疫,她終在六月底帶着僅餘的百多元返港,並於大角嘴的公園、天橋底,甚至公廁等地露宿,幸好後來找到售貨員及食肆侍應的工作,日薪約五百元,而且包兩餐,至少能維持生活。本月初,她在社協幫助下,申請到非政府的資助宿位,「終於有個安身之所,有返安全感。」
快餐店度宿 禁堂食失容身之所
三十五歲的阿明,原在機場做貨運,疫下他留港工作賺錢,育有兩名稚齡子女的他,每月要給內地妻子一萬多元家用。他曾為「慳錢」在東涌露宿,其後因開工不足轉職地盤,並獲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安排入住臨時宿位。不過,他最終回到街頭,隨工地位置改變露宿地點,如較早前在屯門工作,入夜便到地盤附近的公園露宿,至翌日開工。

原在連鎖酒樓集團當「頭鑊」的強哥,前年爆疫後曾棲身二十四小時快餐店,其後政府祭出禁晚市堂食令,他隨即被裁員,連快餐店亦無法容身,被逼露宿街頭,直言難忘「天寒地凍又落雨,凍到手腳麻痹睡不着。」幸獲社工安排入住資助賓館,月租二千七百多元,「總算可以安定下來,而且有工開,不必食老本。」
關注露宿者權益的林國璋牧師強調,露宿者已是全港性的居住問題,希望新一屆政府能協助解決難題。
全文刊《星島》「每日雜誌」